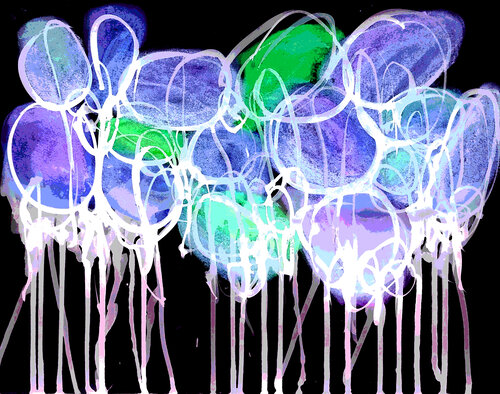喜愛閱讀的人不難發覺,比較中、英文出版界,有一些類型在中文書之中比較缺乏和遜色,遠不及英文書(以至整體西方出版界)的興盛,其中一個類型是名人傳記/自傳/回憶錄(下文統稱「傳記」)。傳記在西方出版界可說是專門的類別,在內容、體裁、資料考證和寫作方法等方面均有嚴謹的要求,在書店也有專櫃甚或獨立部門。反觀以中文為第一撰寫語文的傳記不多,內容也往往不如西方的嚴謹。出現這個現象,相信除了因為中文書市場較小以外,更與華人社會的文化有關:很多華人都沒有要為自己的歷史留下正確紀錄的想法,而且重視與人為善,不會輕易月旦曾與自己交往的人有甚麼是非功過。
基於市場需求,會撰寫傳記的名人通常有幾類,除了政、商、宗教、體育等界別的以外,自然也不乏來自演藝界的。這些演藝界人物的傳記,如果內容翔實,有鮮為人知的資料,其實會成為流行文化歷史中重要的一部分。香港流行音樂工業過去數十年雖然曾經極為蓬勃,對多個華語地區均造成重大影響,可惜曾有人為之作傳的音樂界人物不多(見下文),對於補足香港流行音樂歷史之中的空白幫助不大。因此,香港著名作曲家兼結他手、「達明一派」成員劉以達最近出版自傳式書籍《方丈尋根記──前傳》(2022年,Tats Production出版),實在值得大眾重視。

劉以達在香港流行樂壇的地位自不待言。他和黃耀明合組的「達明一派」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出道,以類近當時西方最為熱門的「電子流行樂」(syn-pop),或稱「新浪漫」(new romantic)的風格令香港樂迷耳目一新。「達明一派」和同期出道的樂隊Beyond影響深遠,至今仍在眾多華語地區中為年輕一代受落,可躋身香港流行音樂最具代表性人物的行列。他們的成長背景和所受的音樂薰陶,又有別於60年代開創香港歐西音樂熱潮一代的樂隊,如Teddy Robin(泰迪羅賓)& The Playboys和許冠傑任主音歌手的The Lotus。所以,劉以達一代的流行文化故事,有需要以文字記錄下來。
嚴格來說,《方》書不單是「書」,內裡除了文字和大量珍貴舊照片外,更有劉以達自己繪畫的漫畫,以及二維碼供上網聆聽他早年樂隊DLLM的作品和瀏覽其他資料,另外還附送一張他純樂器演奏、用作伴隨閱讀的音樂CD。換句話說,《方》書可算是多媒體的創作項目。這正好顯示,劉以達作為以音樂為主、演戲和視覺藝術為副的藝術工作者,即使在撰寫以文字為主的傳記時,也有突破框框的視野(又或根本無視這些框框)。
從文字風格來看,《方》書也不像一般傳記。傳統傳記講求準確可信,因此描述和用字通常盡量正規嚴謹,即使想增加趣味,也要令讀者不致感到內容誇張失實。劉以達卻似乎完全沒有這個包袱,大部分內容於去年1月起在他的Facebook專頁以連載方式首先發表,行文遣詞用廣東話,間中夾雜白話文字眼,其實是這一代香港人典型的社交媒體書寫方式。同時,他不時用上戲謔式的詞句,令人聯想起他演戲或在傳媒上說話時的搞笑風格,例如描寫自己參加一項結他演奏比賽的初賽:「我一出閘就踩盡油,摩打手較剪腳,一時短傳滲入,一時橫掃千軍……最後一招手指尾拉西,我將呢幾個月所有嘅失落、傷感、挫折、憤慨、迷失與不甘,好似如來神掌萬佛朝宗咁,一次過通乾淨所有在腦海中嘅坑渠。」這種寫法有時不免顯得過分戲劇化,但卻無疑為讀者帶來了頗為新鮮的閱讀體驗。
雖然從上述角度來看,《方》書的形式似乎並不類近傳統傳記,但論內容,卻又有很多地方都符合傳記應有的規格,例如書中開首就交代了自己父母的背景和成長經歷。難得的是,劉以達的敘述有其宏觀視野,包括當時入住公共屋邨對基層家庭的價值,以至80年代他能以畫「行貨畫」賺取外快,源於旅遊業蓬勃等。
對於讀者來說,閱讀傳記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對主人翁的經歷、性格和價值觀有更深入的了解。《方》書在這方面可算成績不俗(作為「前傳」,敘述範圍由劉以達出生(1963年)至「達明一派」推出第二張唱片《達明一派II,Kiss Me Goodbye》(1986年))。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,是劉以達在開拓自己的音樂事業過程中,一直展現真正藝術家應有的激情,不斷反省詰問:作品如何在商業與前衛之間找到平衡點,以及銳意創作具有東方特色的搖擺音樂的心路歷程。書中不時強調,要不忘初心:「搖擺精神,有時唔係你fing得幾行、嗌得幾大聲;Rock,就係你有無令人感染到永遠堅持、永不放棄、永不妥協嘅精神同態度。」

劉以達在組成「達明一派」前的音樂事蹟,在樂迷圈子中早已成為傳奇故事,包括曾組成樂隊DLLM和「東方電子樂團」(簡稱OEO),以及參與灌錄現在已成經典的唱片《Xiang Gang香港》(1984年,其他參與者包括有最早期的Beyond和包以正等)。《方》書對這些情節均有頗為詳細的敘述,為香港流行音樂歷史填補了一些空白之處。劉以達成名前與多位樂壇名人(包括黃家駒、侯德健、「草蜢」、郭達年、陳少琪等)交往的片段,也是鮮為人知的軼事。當然,歷史價值最高的應該是「達明一派」相識和組成的經過,書中以極具畫面的方式,記錄了兩人初次會面的情況,也詳述了由試音到推出唱片之間的多次轉折,成為香港音樂史中重要一章的書面紀錄。
與另一些有關香港流行音樂的書籍不同,《方》書較多描述音樂創作和製作的細節,由劉以達早期以一部雙卡式、四軌錄音機,在家中實驗錄音,以原始方法製造多層次的音樂,以至後來怎樣用電結他和電子合成器(synthesizer)來創作五聲音階、帶有中樂味道的旋律,書中均有解說。對於了解粵語流行樂藝術和工業,這些內容都極具參考價值。
總括來說,《方》書雖然篇幅不長,內容頗為豐富,即使組織剪裁間或顯得有點零碎,但卻別有像聽朋友講故事的親切趣味,同時也具備傳記文章大部分應有的內容,值得對香港流行樂發展有興趣的朋友一讀。

記憶之中,香港流行音樂歌手和樂手的傳記書籍不多,較嚴謹的大概只有泰迪羅賓、許冠傑、譚詠麟和Beyond(以上世紀60年代出道的起計,其他藝人的或許只可算是提供主人翁相關資訊的書籍,未達到傳記的水平)。上述傳記中,較出色的是香港大學前社會學教授吳俊雄撰寫、獲許冠傑授權的《此時此處 許冠傑》(2007年,天窗出版)。作者訪問了許冠傑和其他多人,對許冠傑的音樂事業有詳盡描繪,加上吳俊雄以本身的社會學訓練,宏觀地剖析了許冠傑作品與香港社會發展的關係,即使個別環節未夠詳盡,仍不失為香港流行樂歷史的重要作品。
除了歌手或樂隊的傳記外,還有一些書籍以香港流行樂壇歷史為題材,撇除談論歌詞的,至少還有黃志淙和Muzikland所寫的書籍,而筆者認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信佳撰寫的《港式西洋風──六十年代香港樂隊潮流》(2016年,中華書局出版)。顧名思義,該書追溯了多支60年代唱英文歌曲為主的樂隊(也有個人歌手)的歷史,其中部分在今天本來早已湮沒無聞,獲得作者翻查資料,為他們留下紀錄,實在是重大的貢獻。
但是,香港流行音樂歷史值得和需要補遺的地方仍有許多,而且早年出道的幕前幕後人物不少已屆古稀之年,小部分更已去世,記錄相關歷史的工作刻不容緩。相比之下,香港電影工業的歷史研究至少有香港電影資料舘專責在做,但是音樂方面卻完全沒有類似的資源,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應該考慮推動和資助相關工作。